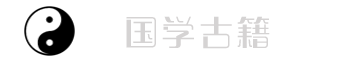我的旧书癖
回想起来,我的天性跟自然是亲近的,与书很疏远。小时候最爱一个人在野地里疯跑,采弄各种野生植物、昆虫、石头,静观白云奇妙地变幻,夕阳悲哀地沉落。八九岁时沉迷蛐蛐,父亲为此揪过我的耳朵,先生像玩排球一样往墙上磕碰过我的头,那时我最讨庆的就是书本。后来我能和书结缘,实是“拉郞配”的结果,出于近乎贞节的美德观,也便“嫁书随书”,到死从一而终了。但在几十年中因此孳生出的许多癖性,像吃臭豆腐一样,自己咀嚼起来殊觉滋味无穷。
先说藏书,我到底藏书的什么?版本?内容价值?似乎都不是。自己分析起来,更多的是收藏着岁月,收藏一种破旧的回忆。我父亲是一个乡村教师,除了教学生,村里人过年的春联最爱他来写,死了人要他写铭旌,盖房上梁先得由他在红纸上画好八卦太极图,谁要出外办大事,先要找他选择良辰吉日,连许多病人的药方也常常求他鉴定可服不可服。此外,父亲也能犁地,也能扬场,1949年深秋,他还在发水的灞河上持杆放过几十里木排。我祗今所以是杂家,大约因了血管里流的本是杂家的血。父亲手上经过而留下来的书,虽然寥寥不多,但却很杂,除了各种木版的、石印的儒家经书外,还有一本二十年代的新诗别集《心的徬徨》,作者是杨宗禹。大约现今专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,也未必知道这本诗和这个诗人,而我少年的诗情,却全是这本诗集引发起来的;一本《给青年的信》,是蒋光慈与爱人的通信集, 我早恋写情书每每剽窃此中的词句和情调;一套石印的《寿世保元》和木版的《本草备要》,没有书看时也姑且拿起来读。再次就是三十年代出刊的一种杂志《教育短波》,另外还有《论说精华》、《麻衣相法》以及三四十年代的中小学课本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。这些古籍在我青少年时代伴我度过了许多个寂寞的雨天,是我精神和心灵栖息的一块隐秘的天地。参加工作后的几十年中我搬过近十次家,每次对这些旧书都是重点保护,首先搬进新居,所以至今大部分还保存着。其中几十本《教育知波》和一张门扇大的黄纸木版印制的父亲中考的喜报,我特别保存在老家伙房的竹笆楼上。胞兄胆小,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开始,红卫兵还没有出动,他先一把火都烧了,使我至今惋惜不已。
再说买书,我曾坦白宣示过我的吝啬,但见到喜欢的书时,则变得比常人大方。一般读书人大都如此,算不得癖性;而我买书时的好买杂书、怪书、旧书,则是独有的乖张。一般人对书,总是看重正规的、经典的、大部头的,我对这类书敬而远之,就像生活中权贵给我引起的那种感情;而对那些不被人注意的怪癖书则兴趣特浓,这也许是经济拮据产生的一种变态心理,积久遂成习性。在西安上大学时,我的星期天基本上都是在南院门的古旧书店度过的。逛古旧书店当然也从阅读中增长知识,但那更多的是一种情的安顿,很像谈恋爱时和情侣的接触、游冶、交流心灵。如发现一本能吸引我的书,呼吸猛一停止,心鹿儿咚咚跳着,而这往往是一本薄薄的、发黄的旧书,内容又往往是谈奇事、凡事、真事、琐事。我把书反复翻看摩挲,身上钱不够时,趁人不注意便把它塞在书架一个隐秘的地方,免得同好者发现。也许转了一会忍不住又拉出来再看一看,看完后一定会选择一个更隐秘的所在藏起来,等待凑够了钱来购买。至今还被我珍藏着的黑麻纸单行本梁启超的《清代学术概论》、排得很疏朗的赛珍翻译的《瞬息京华》、一九三九年出版的章衣萍的《随笔三种》、民国初年范紫东自印的《关西方言钩沉》、道光六年合阳人贾风仪手写未刊的《土音杂字》等,都是那时在古旧书店拾掇的便宜货。
近年来生活已温饱无虞,买书的钱当然活便得多了,但喜买的仍是杂书、僻书、旧书,如谈蟋蟀的专著就藏有五种;长期搜集的民间秘藏方术书数十种,偶一示人,常使一些乐此道者垂涎三尺。这些,大约也可以在一般藏书人之前聊且夸口罢。
买书藏书干什么?其实很少去读,主要是供我把玩和获得一种拥有感。我在寒舍中不会有太无聊的时光,如果没有当紧的事情要做,一不小心就翻腾起藏书来。这等于翻腾已逝的岁月,当一段往昔的眉批留住我时,新我与旧我相互注视、审度、叩问,产生一串人生的况味。玩味那笔迹的稚嫩,追寻当日写这段话时的思维轨迹,旧我在新我前显得委葸自惭,新我又以自己的老迈对旧我朝气产生了嫉妒。偶尔也会翻出在书中躺了几十年的红叶,上头用小楷写着于祐的流红诗。有时翻见的是参观展览的门票或信手涂抹的漫画.....这些零七碎八的劳什子,比我照镜子看到满脸的沟壑和脱发的秃顶更能使我惊骇时光的流逝,人生的匆促。随兴所至,我可能会把这本书阅读一页半页,甚至整章整节地读下去,就像回到儿时玩耍过的河滩,从忆旧中拔出来刚要离开,却又连连发现了造型、花纹都很有意味的卵石,于是浸沉其中,不能离去。有时本来是在一本书中查阅一句话,却流连于久违了的好几本旧书,一上午时间便匆匆过去。到下午,我索性把整架的书重新调动排列一番,像老葛朗台关在钱库里检弄他的钱币,一种惬意的占有感和充实感使我比什么时候都心境舒适。
这二年,新书出版得非常多,价钱一天比一天昂贵,但内容重三复四,错讹随处可见,使我对新书产生了反感,而对书架上的旧藏就益发看重。
此文煞尾,我忽然蹦出一个怪想法:一个人对旧书的倚重,是否透露了他真实的心性和人格结构。他对自己的一切旧物都依恋珍重,由此推测,在家庭的地质结构出现活跃期而往往酿出地震的当今,只要老婆不背叛我,我所处的将是一个无比稳固的家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