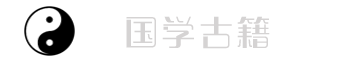昔日昆虫今何在
在回归园田、融入自然、忘怀一切的日子里,一个八十老翁的心灵便纯化成赤子少年,整日在田野里寻觅当年日夕相伴的各种昆虫,可是如今所可见者仅寥寥数种而已,可见物种灭绝之迅疾。
网友可能会说这样是玩物丧志,无聊;我则以为能有此闲趣,实我精神之幸也。与虫为友比起与人为友来,不需要防范,放弃了戒心,自心也变得纯净空旷。友虫一日,快乐一日;往大里说,《昆虫记》作者法布尔以此成事业,我辈对玩虫岂可小之哉!
不要说我玩物丧志,这样说太一本正经了,同时也违背圣人的诗教。孔圣说:“小子何莫学夫诗!诗可以兴,可以观,以群,可以怨,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,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你们何不好好读读《诗经》,诗可以抒发灵感,可以认识社会事物,可以建群交朋友,可以提意见发牢骚。用诗中揭橥的道理作指导,身处江湖可以孝顺父母,身居庙堂可以效忠君主。从中还可以认识鸟兽草木的名字。孔子这话告诉我们,从诗三百首中准确弄清各种昆虫的名目和习性,也是诗教的内容之一。
少年时我玩蛐蛐入了迷,可以说已经达到研究的深度。不仅是看它们咬斗,还给它们建了各式接近自然的土窝,放置了有利它们成长的食物,看它们怎样成长,怎样恋爱,怎样产卵。
蛐蛐的兄弟族类其实是很多的,不是玩蛐蛐我是绝对不会知道的。与蛐蛐形貌相似而个头硕大的是油葫芦,俗称促织织,一到暑天,耕过的土地里遍处都有它们的身影。它们不像蛐蛐儿有固定的窝,而是随处乱窜。蛐蛐基本为一夫一妻,个别也“齐人有一妻一妾”者,油葫芦则是乱婚,毫无贞节。蛐蛐儿性烈好斗,油葫芦并不互咬。
还有一类叫棺材头,我乡称“逼土㒎”,它的头像被削了一刀,又像犁铧上配的“逼土”,它们多居住在草里,叫声无力,珠-珠-珠-珠,听着慌里慌张的。
再有一种叫猪嘴,形状甚像蛐蛐而身短头大,笨头笨脑的。嘴长,像老黄瓜的把儿。它们也斗,但不咬,只用头抵。因数量少,只在阴湿天听到它孤寂的叫声,豆儿-豆儿-豆儿,给人寂寞的感觉。
在我乡湿地的水草中,有一种形状完全像蛐蛐而身量只有蛐蛐一半的,叫声富有金属的脆亮,是蛐蛐的小人国角色。
在上述每一族类中,又有种带翅者。带翅者就是在可以磨响的硬翅下生有白色的软翅,有些可以一蹦飞向空中。
如今蛐蛐还在,棺材头只在晚上听见有鸣叫声,未见其形,其他各族类殆已灭绝。
在我玩过的昆虫中,除栖息在椿树上的一触碰便蜷起来装死的“羊撘狗”和长着花丽翅膀一蹦便飞向空中的“花媳妇儿”外,玩得最多的是金龟子。金龟子俗名“金巴牛”,墨黑色的背上长着金银相间的斑纹。“金巴牛弹弹,一下弹到蓝田。蓝田娃儿逮住,拿个红线线儿拴住。”这是玩金龟子时吟唱的歌谣。村里常有榆树或构树罹病树杆上浸出液汁,金龟子和马蜂便聚上去吮吸,小孩子避开马蜂逮住金龟子,用细线拴在它大腿上,放开让它在空中旋飞,好像放风筝一样。我那时若碰见树杆上聚了金龟子,激动得停了呼吸,心脏咚咚地跳,不像发现了金龟子,倒像拾到金子似的。这些虫子如今都难见到了。
还有一种打发过我寂寞时光我很怀念的土蜘蛛,这一回也没有找到。我叫它土蜘蛛,是因为它是生活在丘陵地带的土坎土窝中,并不在空中结网。它也有网,但它的网只有巴掌大,并不是经纬织成的省丝的充满空隙的大网,而是绵密得像一片灰色的绸子,罩在它居住的坑窝上,一旦有蚊蝇蟋蟀之类误触网上动弹不得,它就一下从暗处冲出饕餮美餐。有时它也有顾虑,在网边迅速闪几下才向猎物下手。我放牛的时候,常常恶作剧地捉些蟋蟀幼虫扔在网上,观看土蜘蛛的狩猎表演。
故土家园触发了我的前尘旧梦,从梦中醒来遇到的是无言的寂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