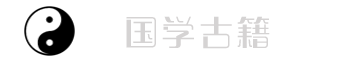为任劳任怨的驴子正名
驴子世家
我自己也弄不明白,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,便常常为驴子鸣不平了。
本来,驴子和黄牛都是农家之宝。它们一道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;主人们的衣食住行,大都出产在它们身上。黄牛确是有股牛劲,在与驴子的合作中,自然多出了许多力气。但它不认为自己是吃了亏。驴子呢,也憨态可掬。场光地净之后,黄牛休息了,女主人却要它驮着走娘家。对此,驴子也没提出异议,说是应该与黄牛轮流着驮。一个俊俊巴巴的小媳妇,横坐于银灰色的驴背之上,颠儿颠儿地,又风采又爽当。要是让她坐上牛背,“驾!驾!”地吆喝着,一步三喘气,成何体统?由此观之,牛与驴对于农家的贡献,大体是相当的。至于李聃老先生,曾骑着青牛出关,无疑是牛家族的一桩盛事。但驴子与此相比,也逊色不到哪里去。张果老张老神仙,就曾倒骑着它们的某一位先辈,飘飘然仙游天下。我国新疆地区的人们,把死了的驴子的四脚,牢牢埋在路边,让它成为指示行人的路标。这作用,它的牛兄办得到吗?
可是,我们最讲究敦厚公允的祖先,却无端弄出一个牛尊驴卑来!他们定出的六畜依次为:牛、马、猪、羊、鸡、狗。这不仅极大的影响了驴子的声誉,而且几乎等于明令取消了驴子作为家畜的资格!这就叫人很不服气。古人定牛为六畜之首,当然没什么不可以;今人拿牛自比,说“做人民的老黄牛”,如能言行一致,自然也是极好的事。但驴子也不至于鸡狗不如——而且鸡狗之下,仍然无名!无名,如果一直无下去,也不能算作顶坏的事。驴子虽然没有“不求闻达于诸侯”的胸怀,它也满可以忍了。劳动者都是美的。劳动着你便美丽着。孰料,辛苦劳碌之后,竟有人拿它的名字,当作骂人的工具。有人说了句什么,别人响应慢了点儿,就被骂作“你耳朵塞了驴毛啦!”唱的或说的,有一两句不合人家的意,便有人骂你:“像磨扇压住了驴耳朵!”在历次运动中,个别分子不那么温良恭让,就有人提议“整他的驴脾气”!更有甚者,人们种了一种青萝卜,也起名“绊倒驴”。说这种萝卜大,地面部分其高盈尺,产量可观,驴子当然不会有意见。但为什么偏要顺带着贬低驴子呢!驴子就那么没有用,萝卜便能将其绊倒?
我这样苛责于人并不是以驴子的代言人自居。我没受过它们的委托,更没拿过驴族的津贴。不过细想起来,这不平之气也并非毫无来由——大约与我的一位隔壁邻居有关。他姓高,叫高驴儿,是与我一块光屁股长大的少年朋友。
高驴儿比我小八个月,比其他伙伴也小些,但却是我们这群光腚猴儿的猴王。乡村的孩子头儿,不是由什么机关委任,也不是所谓民主选举产生,而是在共同的游乐嬉戏中自然形成的。高驴儿就是这样。我们养的家雀,必须装在笼子里时时提着,他养的家雀不用笼子,人走到哪里,它飞着跟到哪里,飞累了便站在他肩膀上歇息。他编的蚰子笼小巧玲珑,入了冬可以揣在怀里,用身子供暖继续喂养。同样是风筝,他的飞得最高。这就赢得了我们的尊崇!就连他脖颈里断断续续的疤痕,都似乎令人羡慕。不过,高驴儿首领地位的最后确立,却是一次集体行窃。
全村的瓜果,只要我们略施小计,便可到手到口。容易得到的东西,算什么屁东西!有一天,我们决定享用“二挤巴”的甜瓜。“二挤巴”其人,眼色不济,两眼成天打闪一般,一挤一挤地眨动。正由于他明白自己的薄弱环节,对于瓜田的守护,才更加严谨慎密,常常使我们望其瓜而兴浩叹!行动之前,高驴儿要我们在水沟边站好。他挖了许多黄泥,挨个儿朝我们身上糊。我们从头顶到脚跟,都给他糊了个严严实实,只露着俩眼儿。他告诉我们:万一被发现了,万不可撒腿便逃。二挤巴腿长,逃不脱他的追赶。要原地趴下。行窃是傍晚时分开始的。二挤巴不愧为二挤巴,他发现了我们。但随即他就失去了目标。我们用与地面颜色相差无几的盔甲,避免了一场被生擒活捉的耻辱,不用说,也躲过了家长的一顿死揍。最重要的,是每人各闹了一只甜瓜进肚,打破了二挤巴看瓜从来不少的神话。就凭这,他不当头儿谁当?
一九五0年,村民们按地亩拔钱,在漫野地里盖起一所房子,办起了小学。在村长的动员下,父母允许我们去念书。猴王高驴儿率领着他的猴儿们,欢欢喜喜进了校门。入学第一件大事,就是起大号。教员是一位教过许多年私塾的老先生。他给高驴儿起了一个极好的名字——高德民。现在想起来,这位老先生的意思,大概是让他有德于民吧?可是,他只上了三天学,便被他爹要回去了。他爹买了一头驴子,必须由他割青草喂养。因此,“高德民”三字,便很少有人知道。他自己也觉得,像借了一件什么东西,用了三天之后,又原样还给人家。他仍旧叫高驴儿。
即使如此,高驴儿还是超过了他爹。他爹从未有过大号,人们只唤他的乳名“大发”。他是个极有力气的汉子,啃山为生。他用《水浒》上写过的那种江州车子,一次推两个喂牛的石槽,还要外加一只捣米的碓窝子。乳名是父母美好愿望的寄托。他出了无数的力,却老是发不起来。但高大发不相信有力气发不起家。他立志置土地,喂牛马驴骡大牲口!大约是为了预测一下自己发家的前景吧,他把三个儿子分别起名为:大牛、小马、骡子。可是,不幸得很,他们各活了三四岁,约好了似的,一个接一个地死了。连死三个儿子,老婆哭得无数次死去活来,高大发本人却并不怎样伤心,只是为这极坏的兆头丧气。儿子们生病的时候,他不请先生医治,照样去啃他的山。第一当然是没钱,更重要的是,他认定,如果自己命里有大牲口,他们断不会死;如果没有,就非死不可,花再多的钱也留不住。正当他十分懊丧的时候,老婆又给他生出第四个儿子。高大发的心中,又升起五光十色的希望。不过他再不敢高攀,只给他起了个高驴儿的名字。没有前三种大牲口,驴子照样耕田,田里照样打粮食!不料,高驴儿长到六岁,又突然生了病,是害蝼蛄疮(淋巴结炎)。这回高大发沉不住气了,再不去啃山,蹲在家眼睁睁守着。但一如既往,仍不给他请先生。后来不知听谁说,蝼蛄疮可以用蝼蛄治,叫做以毒攻毒。于是,他便每天扛一把抓钩,从地里刨两三只蝼蛄回来,装进大葱的叶管,再把葱叶卷入烙馍,瞒着高驴儿吃下肚去。这方法倒也灵光,半年之后,蝼蛄疮除留下晶亮的疮疤,居然完全好了。儿子大难不死,高大发高兴至极。由此他坚信不疑地认为,自己命里还有一头驴子!于是,他用土改后的第一次收获,买了一头驴驹儿,四脚伶仃,蚂蚱似的。有小不愁大!他也不再去啃山。
过了两年,高驴儿用他割的青草,把驴驹儿养成了一头壮驴。银灰色,强健的四腿,硕大的躯体,年轻而又俊美。高兴了叫一声,三五里内的草驴听见,都一片声地响应。说句不怕遭骂的话:它是驴中的美男子,是草驴们心中的太阳!
开始,不知高驴儿是怀念他的部下,还是恋念他三天的学生生活,只在学校附近割草。我们下了课,也跑去帮他割。他看着不久前还属于他的部下,目光里闪动着畏怯和慌悚。我们看着我们不久前的头领,心里充塞着凄楚和悲凉。后来,驴驹儿日长夜大,食量不断增加,学校周围再割不出多少草,他不得不到离学校远点的地方去割;再后来,他愈割愈远,久而久之,我们便失掉了自己的首领。他呢,也失掉了他的部属。
他爹倒快活起来。喂草驴的人家,求他的驴子配驹,无论是谁,他都满口答应;无论手里忙着什么,也都赶紧丢下。他指手划脚,吼天吼地,给予原则而又具体的指导,好像他是某农学院牲畜系训练出来的驴子配种权威。有一次,在指导配驹结束时,被洒了一头驴精,他只不在意地用手抹一抹,又继续去喝他的山芋大渣子粥。因此,在不太长的时间里,他这驴子的驴子驴孙,就遍布了附近几个村庄。使高大发最感骄傲的,是借他的驴子娶媳妇,这不是求他,而是给他去送荣耀。但你至迟必须在头天晚上告诉他,以便使他来得及炒些黑豆,对驴子进行犒赏,来得及用刷子和梳子,对驴子加以梳妆打扮。他有自备的红绸和串铃,临出门挂上驴的脖子。准备工作细致周到,严肃认真,像办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。村人每夸谁家媳妇漂亮和贤惠,他会再三强调:“那是我的驴子娶回来的!”人家承认这事实之后,他就像喝醉了酒,神志恍惚,心荡神摇。也只有在这时候,他才会突然想起儿子的割草之功,急急地奔进屋去,拿出一只生鸡蛋道:“喝了它!这东西败火,太阳底下搁得住晒!”奖赏过儿子,如果我们也在旁边,他还会教大家唱几句歌谣:“大姑娘,二姑娘,胡子长到大腿上!”我们自然弄不明白:姑娘怎么会有胡子,又怎么会长到大腿上去。高大发不管你懂不懂,仰起长长的马脸,只管声音极响地笑。
我们升入高小之后,村里成立了初级社。不久,初级社转为高级社;又不久,高级社转为人民公社,还开展起大跃进运动。高大发预测得清楚,自己命里有一头驴子,可他没有预测到,驴子之外,还有一个近在眼前的共产主义。“大要劲”不就是大出力吗?有攒下的钱财,没攒下的力气!目前多的就是这玩意儿。又给这种种好处,憨熊才不干!于是高大发带着儿子高驴儿,嘻嘻哈哈,张张扬扬,去炼钢铁、挖水库。在运矿石和土方中,队里分了一头驴子,给他的车子拉梢。他不要。他指指儿子:“我有驴子哩!”高驴儿从割草喂驴子,变成了一头拉梢驴子。
历史是位满把胡子的老头儿,他不喜欢人家跟他开玩笑——浮夸终于造成了浮肿。高大发比别人浮肿得厉害。他力气大,食量也大。后来脚肿崩了皮,无休止地流黄水。两个月之后,这个一车能推两个喂牛的石槽外带一个石碓窝子的大汉,便悄没声地死了。他死得很满足。自己这辈子终究没白活,曾经喂养过一头真正的驴子!这是在另一个世界里,可以炫耀于列祖列宗的业绩。但他没有想到,他的儿子久后一日,更加可以自夸于他。因为高驴儿埋了他爹回来,队长就立即通知他:“派你到饲养室,专门去喂驴子!”
高驴儿饲养驴子,完全是队长忽发奇想的结果。原来驴子这动物,不知是过不惯集体生活,还是为没过上“点灯不用油,耕田不用牛”的日子而气恼(不用牛,还会用它们驴子吗),便一头接一头地死。每死一头驴子,社员们就喝一顿透鲜的驴汤,阖村老少都很满意。队长可是焦愁坏了。饲养员一茬一茬地撤换,驴子还是一头一头地死。队长读过几句书,一定是福至心灵或者情急智生,他忽然想起了高驴儿。同病相怜,同名是不是也会相怜?
高驴儿走马上任(应该说是走驴上任),重操旧业,驴子死亡的速度,果然放慢了许多。只在一年半载,才有一头寂然作古。社员们喝着这一次的驴汤,几乎想不出上一次喝驴汤的日期,大家都很遗憾。高驴儿爱养驴子,真的作怪!队长却十分得意。他感谢自己的想象力,到底一笔写不出两个驴字!驴子对于高驴儿,总要讲些面子,决不经易让自己的同名伙伴丢脸。高驴儿对于驴子,自然要比别人关切些,不肯让自己的同名伙伴渴着、饿着。
当时的农村,有一个心照不宣的规矩: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。队长、会计、保管员三大巨头,掌管仓库的钥匙,就吃仓库;社员在大田里抓工分,就吃大田。高驴儿饲养驴子,吃不吃驴子,我不清楚。因为这时我入伍服役,而且一干就是十九个春秋。但我毫不怀疑,高驴儿的几位前任,是绝对吃驴子的。
每次探亲,我都要到饲养室,去看看我儿时的朋友。高驴儿日渐瘦弱,日渐衰老。但每次见着他时,他都在为驴子操劳。一遍一遍地筛草,一遍一遍地淘草,很吃力地运土垫驴脚。他的微笑是麻木的,动作是迟缓的,目光里再没了当年割青草时的卑怯和慌悚,这表明他对目前生活的安然确认。那些驴子跟他一样,也失去了盛世气象,一头头瘦骨嶙峋,蔫头蔫脑。高驴儿的几个孩子,跟他爹和他爹养的驴子相比,相对好一些,虽也既黄且瘦,却无大疾病上身的形迹。他们降生的时候,高驴儿和他头发极少的女人,也许给他们起过美好的乳名,可惜村民们不予承认。驴子的儿子还能叫什么?只能叫驴子!又因他们数量可观,品种一律,大家依次呼其为大驴儿,二驴儿,三驴儿……至此,已形成了一个驴子世家的局面。可是,在高驴儿家里,人人都忌讳一个“驴”字出口,他们称它们为“大耳朵”。
一九八0年初,我转业故乡县城工作。村上常常有人进城,我也不断回去看看,有关高驴儿及其驴子的消息,也便滚滚而来。
分田到户的时候,队长也老了,但头脑还像以前一样灵活。房屋,农具,树木,这都是好东西,他不愁没人要,愁只愁那头将死的老驴。这时,高驴儿找上门来,表示要那驴子,而且态度十分坚决。老队长喜出望外。为了把他砸得实些,难以反悔,便说:“你要它干什么?破货了。”高驴儿说:“你甭管!”老队长当然愿意给他,可他极善联想的脑子,无论怎样苦思冥想,也想不出他要这破货的道理。最后,不得不再次动用“同名相怜”四字。只有用此四字,才能解释得清爽。
高驴儿分得的驴子,不是牵回家的,而是请大家帮忙,抬回家的。它已无力站起,更不能走动。为此,高驴儿搭上去两包丽华香烟和一瓶老白干酒。
全村噪然哗然!村民们本想用它熬一锅透鲜的驴汤,以便让自己喝下两碗,痛痛快快地向旧生活打个招呼分手。谁知竟被这老怪物搅了!世上万事万物都不是孤立的。高驴儿分去驴子,给大家造成了不快,但驴子省下的那部分财产,又使大家得着了安慰。村民们转而高兴起来,当面跟高驴儿开玩笑:“你请个驴爹回家养老吗!”更多的人是在背后议论。他们分成两派。一派说,高驴儿养驴肯下苦,说不定能把它养壮了,给他出一份老力!另一派说:“什么肯下苦!二十几头驴子,还不是差点儿给他养光了!”这些议论,高驴儿到底是听到了,还是没有听到,人们无法知道。因为高驴儿从未对此发表过任何意见。他能说什么呢!自己肯下苦和养死了驴子,这都是事实。对事实是无法否认的。
驴子被安置在一个套间里,高驴儿蹲在地上,两眼湿漉漉的,定定地看着面前的驴子。驴子瞪着黑褐色的眼珠,瞧着自己的新居。地面铺着暖和的干草,房顶开着明亮的天窗。它一进了这地场,就立刻感到,比在饲养室受用多了。这饱经忧患的驴子,不知道人世间又起了什么变故,使自己到了暮年晚景,又得着了如此厚爱。
高驴儿没有像他爹一样,家里有了驴子,便让儿子停学。但他严厉地命令他们:放学的路上,必须割一些青草带回。于是驴子的食槽里,便有了四样东西:干草,青草,麦麸,炒豆。高驴儿对驴子如此孝敬,村民们又嘲笑起来:“高驴儿,你给你驴老子顿顿吃四样菜,还差一壶酒哩!”高驴儿只和顺地笑笑,依然不吭声。孝敬和四样菜,同样是事实,同样无法否认。
驴子吃着营养丰富的伙食,身上渐渐有了力气,经过许多次的失败,最后终于站了起来。像庆祝自己的胜利似地,竟还嘶哑地叫了两声!这是高驴儿的节日!他爹听人家夸奖他的驴子娶来的媳妇又漂亮又贤惠的时候,当年曾经如醉如狂过。高驴儿现在也一样,看着站起来的驴子,听到久违了的叫声,捣动着两条早已丧失了灵活的细腿,原地跳了两跳,咧开嘴嘿嘿地直笑。他大概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。他笑得坦诚,笑得天真,笑得动人。在高驴儿的节日里,我来看他,排除他满脸胡髭和皱纹的干扰,我几乎看到了我们当年猴王的形象。
我心里却十分戚然。当年,如果他爹不买那头驴驹儿,或者虽然买了,而不把他从学校叫回,凭他出众的聪明,他会成为一个时有革新成果的工人,或者一个卓有政绩的干部,甚或是一位屡出科研成果的大学教授。为了驴子,这些他都失落了,还捎带着失落了他的爱情(他娶的是一个秃女人)与他极好的名字!然而他自己并不觉得,竟为一头驴子的转危为安嘿嘿大笑!啊,我可怜的头领,我永远逝去了的猴王!
驴子属马性,喂过草料,必须遛一遛,这是几个小驴儿的任务。动物就是动物,身上有了力气,便又想起调皮。有一次四驴儿恼了,威胁道:“再跟我捣蛋,还把你送到队里去!”高驴儿听了,大发其火,咆哮道:“放你娘的狗臭屁!它要是回到队里,也没他妈你的好日子过!”驴子偶染贵恙,高驴儿并不牵着它去兽医站求医,而是把兽医请到家里,好烟好酒招待着,慢慢与他调治。所幸站里不只一位医生,否则只有闭门谢客。驴子康复,高驴儿放行,兽医们每次都有囚徒遇赦之感。
驴子强壮起来,张驴儿却不让它下田劳作,依旧把它闲养在家,仿佛它不是一头牲口,见天要消耗数量可观的草料,而是一种珍贵的鸟儿,养着它可以享受田园之乐,可以陶冶性情。每逢耕田,张驴儿总是伸着头、弓着腰扶犁,小驴儿们也总是伸着头、弓着腰背绳。爷儿五个汗流浃背,像刚刚出水的虾米。历史有时会出现惊人的重复。过去高大发把儿子高驴儿变成拉梢的驴子;现在,高驴儿又把自己的儿子——小驴儿们,变成了拉犁的驴子。所不同的是,高驴儿作驴子的时候,是为共产主义所吸引,没有半句怨言;今天小驴儿们作驴子,尽管面前是属于自己的丰收,却不断地立眉竖眼,发些牢骚,高驴儿只一味装聋作哑,照旧赶他们耕田。有一天,小驴儿们终于忍无可忍,一齐扔下了绳子,异口同声质问他爹:家里明明养着四条腿的大耳朵,为什么偏用我们两条腿的!在高驴儿看来,这无异于一场罢工,一场暴动,一场反叛!他抽出了腰间的鞭子。他像一个极富经验的奴隶主,知道奴隶们不会安分地为他劳动,便预先随身带着刑具。他朝儿子背上抽打,打一鞭,恶狠狠地骂一声:“没良心的东西!我单打你们这些没良心的东西!”小驴到底拗不过老驴,最后还是伏首听命,下死劲拖那沉重的木犁。
驴子毕竟太老了,最终寿终正寝。它是无疾而终。村民们又兴奋起来,每家都打算称几斤驴肉,重温一下驴汤的滋味。老队长拿定主意,买那条驴圣。过去死了公驴,这东西都是一律归他的;此物极为壮阳,其味道且可与熊掌、驼蹄媲美。更有精明的人,拨动心头那把肉算盘,替他算计皮张的价值。可是出乎意料,高驴儿命令他的小驴儿们,合伙抬着,把它安葬进了自己的责任田。
挖掘墓坑的时候,我回家碰上了他们。高驴儿主张挖深一些,以防今后用拖拉机耕田,动着了它的遗骸。小驴儿们却想偷懒耍滑,这又使高驴儿十分恼怒。大概恼怒得过了头,竟不顾他当年的猴儿在侧,有失猴王脸面,蹲在地上大哭起来。他热泪滂沱,边哭边骂:“你们这些没良心的东西!指望我养活你们,我哪来恁大本事!要不是你们吃了大耳朵的黑豆,你们一人三条命,如今也用完了!”
我听了大吃一惊,原来同名并不相怜,驴子也吃驴子!这大约是老队长当年没想到的。高驴儿饲养驴子,死亡的速度所以那么缓慢,是他刻意在水与草上下苦功的结果。驴子是吃夜草的动物,为了维持生产队的畜力,为了维护孩子的生命,二十几个春秋,七八千个日日夜夜,他该付出了多少辛劳!
驴冢很快筑起来了,孩子们跪在冢前。四个小驴儿,虽然年轻,也是万物之长的人类的成员,此刻却给一个动物下跪,而且并不是为了他们本身的过错。我可怜着孩子们,把他们一个个拉起,叫他们先回家去。我陪着高驴儿,低着头,在驴冢前站了很久。我们默默地站着,谁都不想说话。高驴儿在想什么呢?他心里一定很悲怆,很难过,很歉疚。驴子们用它们的口粮,先后养活了儿子们二十多年,他和儿子只报答了五年,时间太短了!他也一定很高兴,很欣喜,很感奋,他毕竟埋葬了一个时代!
为了地下和地上的驴子,为了四条腿和两条腿的驴子,我便常常地鸣不平了。但我隐约觉得,这不平之气,似乎并不是在驴冢之前产生的……
公众号:肉糜余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