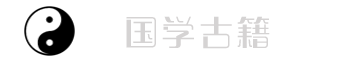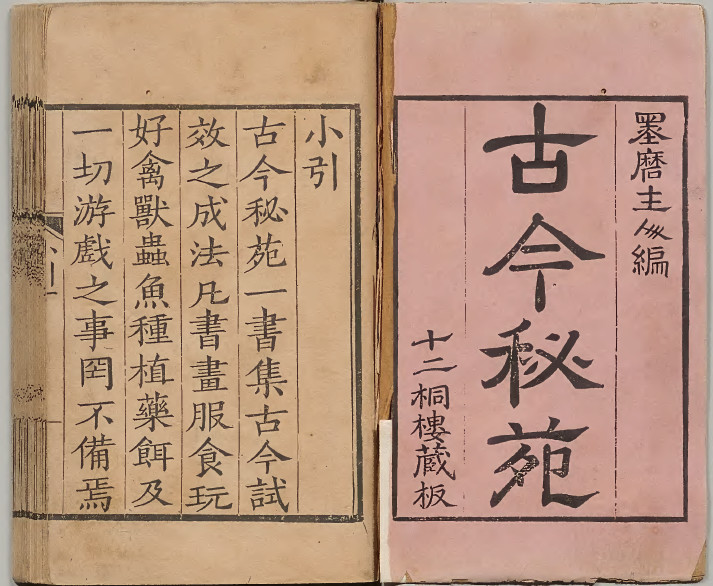回忆我小时候玩的游戏
第一件想到的事是滑板车。用松树锯成四个轮子,中间穿个洞套入竹管,再安上一块木板和方向盘,就是我们最喜欢的滑车了。在山坡上修一条斜道,把滑车扛到最高顶,顺道开下来,那种感觉,有如现在一些年轻人在飙车。有的男孩子胆子大,车轮子也做得大,跑的速度快得多,但危险也增大了。由于手控的方向盘不是太灵活,翻车也是常有的事,也有的孩子因此受伤,弄的灰头土脸更是难以避免。但我们乐此不疲,大人们似乎并没有过多地干预我们。
// 夏天水塘就是最好儿童乐园
有哪个农村小孩没有到河里玩过水呢?一到夏天,我们经常去村里的一条河里玩水,那里有个水塘,最深的地方大概有一米。由于没有老师教,我们只学会了简单的“狗爬式”。我们经常打水仗,那扑腾的水花,扬起了我们多少的欢笑!我们学会了在水中憋气,看谁憋的时间更长。也有一两次,我跟着大人去一条大一些的河里游泳,高过人头的水流,让我无法立足,慌乱中呛了几口水。大人们是禁止我们自己去河里玩水的,毕竟危险是存在的(听说之前有小孩子被淹死的事情)。有时放学回家迟了,母亲就问我,是不是去游泳了,我自然否认,这时母亲就要我伸出手,在我手臂上划一下,如果出现一条白色的痕迹,就说明我去玩水了。这时母亲就会训斥我几句,或是在我屁股上打几下,以示警告。但这样轻微的惩罚,又怎么能够阻止一个小孩子强烈的好玩之心呢?
// 神奇的蚂蚁世界
但最好玩的还是捉蜻蜓和看蚂蚁抬尸。蜻蜓可说是大自然的精灵了,它那富于变化的色彩,薄如蝉翼的翅膀,平稳飞翔的姿态,以及立于草尖上的那种静美,都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。如果是几十只,甚至上百只蜻蜓在空中聚集、飞舞,那场景,堪比一部好莱坞大片,壮观极了。但要捉到蜻蜓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有时看它停在草尖或树叶上,你悄悄地靠近,正要出手捉它的时候,它比你更迅速地起飞了。但也不是毫无办法,也不知道是谁想出的绝招,就是用蜘蛛网。找来一根竹杆,在竹尖上安一个竹框,把蜘蛛丝一层一层地缠绕在上面,形成一个结实的蜘蛛网。看见蜻蜓时,把竹杆慢慢伸过去,几乎百发百中。把捉到的蜻蜓去掉翅膀,撕成两半,放在蚂蚁经过的地方。一旦有一只蚂蚁发现了,就会回“家”(洞)去报信,一会儿就有成群结队的蚂蚁出来,这时我们就念起关于蚂蚁搬家的儿歌(歌词已经忘了),看着蚂蚁们齐心协力地把蜻蜓慢慢地抬到“家”里,这样一个过程往往要持续一两个小时。有时,吃饭的时间到了,母亲在家门口远远地叫着,我们还是无动于衷,蹲在地上目不转睛地看着。我们非常好奇,蚂蚁是靠什么传递信息呢,难道它们也有自己的语言吗?蚁群是不是有一个指挥者,是不是也有它们的口号,不然它们的动作为什么这样整齐呢?蜻蜓,蚂蚁,还有夏夜里梦幻般的萤火虫,以及会吐丝的蚕,无止境聒噪的知了,这些我们儿时的“玩具”,它们是多么渺小,又是多么的神奇啊!
//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,酸枣是我们难得的解馋零食。
秋天到了,酸枣树下就成了我们的乐园。我家对面一百来米处的山坡上,长着两棵高大挺拔的枣树,树高有四五十米,树干四五个人牵着手都抱不过来。树下是一条平坦的路,路边有一条小沟。秋天枣子成熟的季节,风一吹,就有枣子掉在路上,台风来的时候,酸枣就落了更多了,这时,抢着拾酸枣就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了。有时一大早,天刚刚亮,我就和大哥一起起床去捡,一般都能捡到一大碗的酸枣。没有风的时候,我们会爬到树后的山坡上,用小石子朝树枝上掷出去,或用自制的弹弓去射,将酸枣打下来。酸枣的肉是白色,味道有点酸,在物质匮乏的年代,它是我们难得的解馋零食。待酸枣落尽,大人们会在树下的宽阔处铺一个打谷场,那时稻草堆就成了我们捉迷藏的理想场所,虽然稻草弄得我们身上发痒,但我们却乐此不疲,无比开心。有一次发生了意外,一个挑谷子的农民从那儿经过,我刚好站在路边,被他不小心碰了一下,摔到了沟里,左眼眉毛处被陶片或是玻璃割了一个口子。时间拉长到2000年前后,一个有台风的夏夜,其中一棵枣树不幸被刮倒了。这棵站在我家门前,像一个卫士一样守护村庄,见证了我们家族历史的老树就这样消失了。2019年,我回到家乡,看到另一棵枣树根部的泥土被乡人挖去做农肥的配料,我担心它迟早也会倒掉,就向有关部门要了点钱,叫几个农民用石头围了,填上土,把它保护了起来。我多么希望它的生命比我的生命更为长久。
// 摔土泡
还有一种玩法叫摔土泡,是把泥巴捏成碗状,然后往里吹一口气,对着光滑的石头狠狠的往下一扣,泥碗的底部就会被压缩的空气炸开,发出“啪”的一声。大家根据泥碗被炸开的口子大小,给对方补偿与口子同样大小的一块泥土,谁得到的泥土越多,说明他摔的土泡最好。有时被炸开的泥土会溅起来,弄脏衣服,回家就有可能被大人骂。
到了冬春农闲的时候,天气冷了,我家门口的那丘大田放水晒干了,那就可以玩一种叫打尜(ga第二声)的游戏。先是截取一根直径约三公分、长约十公分的木头,把两头削尖磨圆(像子弹头那样),这就是尜了。再准备一根约二尺长的木棒(即尜棒)。尜的重量要适中,太重了或太轻了都飞不远。打尜时,可两人玩,人多时也可分成两队玩,以尜打出的距离远近决定谁是赢家。具体打法是,把尜放在一块硬实的地上,然后拿棒轻抬快落打击尜头,让它瞬间旋转跳起来,再用尜棒用力地去击打尜。最好能击头尜的中间部位,这样尜才会飞得远。如果力道掌握不好,只击到尜的边缘甚至没击着,那就自然输了。有时也可以不以远近定输赢,可以在远处画一个圈,看谁的尜落入圈内的多。谁输了,就要被打屁股或钻裤裆,以示惩罚。
// 滑铁轮
小时候玩的项目还有很多,比如打水枪、滑铁轮、跳绳、跳框、下军棋等等。这些游戏,现在想来,虽然简单,但那么自由、有趣,也让我们悟出了许多科学道理,伴随着我们度过童年的时光。
在《忏悔录》中卢梭写道:“无论善与恶,我都同样坦率的写出来,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,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……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,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。”卢梭的真实坦诚,让我很受教育!又有哪个人特别是他的孩儿时代,没有做过一点坏事、丑事或是调皮的事呢?
// 在农村偷木头绝对考验体能
说实在话,我自小是一个特别老实、特别胆小的人,加上长期担任班干部,一直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,我也就格外注意维护自己的形象,尽量多做好事,不做坏事。但也有例外的情况。村里有一家人,从父亲到几个孩子,个个都是狠角色,经常欺负别人,常常把别人(包括我的)晒在山上的木头偷走。有一天,我在路上遇到他们兄弟中比我小的那一个,我问他为什么要偷我柴火,他反而对我大声嚷嚷,说,谁能证明那木头是属于你的。我一气之下(主要是我估计我打得过他),抓住他的衣领,把他顶在墙角,朝着他胸部打了几拳,然后跑到了学校。过了会儿,他母亲带他到学校,当着班上同学的面,把他上衣解开,说是我打的,我撒了个谎,矢口否认。课后,班主任邱老师问我,是不是你打的,我低头不语。为此,邱老师严厉批评了我。
// 学生时代打架往往不知轻重(电影剧照)
还有一次打架,虽然不是我动手的,但与我也有一点关系。在石坑附设初中班时,有许多同学是邻近村庄,如半山、上地、银山头等自然村来的,他们寄宿在村部宿舍。有段时间,为了逃避父母的管控,我也与他们混住在一起。同学们分成两派,各有各的“司令”“军长”等等。我被其中一派推举为“司令”。有一天,对方“军长”带人冲到我们宿舍来,当时我方“军长”正站在床铺上,在吵闹中,我方“军长”突然朝对方“军长”当胸一脚,对方当场倒地。对方这个同学身体非常健壮,平时能挑一百多斤的担子,估计那一脚把他踢成内伤了。我们当时不懂得、也没有条件把他送去医院检查。后来这个同学身体就变差了,四十多岁时英年早逝。我没有问他去世的原因,不知道是不是与当年被踢的那一脚有关。对此,我的内心总有一种不安。
// 心急吃不了烤番薯
还有就是偷东西吃。有时在上山砍柴时肚子饿了,看到路边正好有番薯园,就偷偷地挖出一两个小番薯,用水洗了生吃。如果附近没有水,就用草把番薯表皮的泥巴擦掉了吃。也曾经与小伙伴们,偷摘了几把青色的黄豆,烧火用瓦片烤了吃。在学校寄宿那段日子,有天晚上,几个同学肚子饿得不行,说要去弄点东西吃,作为班长、“司令”的我,居然就批准了。他们先是到一个农民的果园里偷摘了一些玉米,后来又发现了油㮈果,认为玉米要煮了吃很麻烦,就把玉米全扔到田里,转而摘了一堆油㮈回来。我们大饱了一次口福。为了防止被人发现,我们在木地板上挖了一个小孔,把果核一个一个地塞了下去。第二天,那个果农把被扔掉的玉米煮熟了拿到学校来卖,说昨晚有小偷跑去他果园偷了东西。还有一次,他们去偷南瓜,把南瓜朝向草丛的那一半给切了下来……
// 诱人的小尾巴
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。偷东西吃,大概也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现象。人一旦连温饱都无法解决时,对其道德上的更高要求就变得奢侈了。当时邻村有个姓高的知青,更是连猪尾巴都不放过,他先是用手轻轻抚摸猪屁股,让猪感觉很舒服,然后拿块小木板抵在猪尾巴下面,突然举刀砍下去,把猪尾巴砍断了,而后烤了吃,至今村里人还提起,说着那个年代荒唐的故事。
时间过去快五十年了,现在已经看不到有孩子在玩我们小时候的那些游戏了,就像世上许多濒危物种那样,那些游戏也慢慢地消失了。但无论如何,那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记忆,是我们永不磨灭的童趣,每每想起,依旧会心生涟漪,溢满了快乐。
作者:陆开锦 公众号:EXPLORE寻隐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