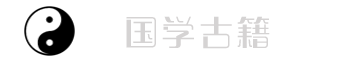阴河记
每次回家,在车站打车,师傅问去哪儿,我都是报七眼井的地名,不用多说,师傅立时调转车头就上路,七眼井虽是个小地方,但小有名气,生意人多,来回家乡的人也就多,师傅们路都是跑熟了的。
县城往东,过黄土岭,是大和堂,横阔二三千米的大冲击平原,沿着小溪往再往东,过黄陂桥、周里桥、子龙桥,桥在溪上跨来跨去,车也就伴着溪水拐来拐去,溪不宽,但终年有水,水是活水,所以一冲的水田不用灌溉,却总是生意盎然,令外人羡煞。
这水是哪来的?总会发出这样的疑问。
阴河的水,我们总是很自豪地回答。
田冲沿着东南边的山坡自东向西推进,梯田也顺势排列,隔一二里地,山脚下就有一口深潭,潭水四季不断,雨季不涨,旱季不枯,夏季沁骨,冬季暖肤,温泉一般,还冒着腾腾热气。 七眼井的地名,据说就来自我们村东边那条小街边的七口活水井,三口井在路边,四口井在人家的屋基下,七口井一串儿排开,据说,那是按照天上七星的位置罗列有序的。所以,七眼井在地方文献中总是乡土文士们咏诵的题材,风物传说也就很是有些神奇。
传说总是不胫而走,于是,整个七十年代,就有一波一波的地质勘探队的出现,钻井尖塔在村前屋后树了起来,往地下蓬蓬地钻洞,钻了不少洞,带走了一节一节香肠似的圆柱形岩芯,再把洞口掩埋起来,然后像来时一样,神秘消失了。
据说,那是国家机密,自然是不让村民知道的。但我们都相信,他们是来找我们的地下阴河的,还说,那水量足足有资江河那样大,将来修了水库,就是半个洞庭湖。
不过我们这边始终没见动静,倒是东边山里砂石公社的岩岭上开始修水库了。
抽劳动力,每村都抽了人去,轮班抽人,每个壮劳力都给轮了一年,抽倒了,自己带上扁担箩筐,半年可以回来一次,回来时挑着一身疲劳,满肚子辛酸,偶尔也有带回一个冲里姑娘的,回家做了大媳妇。
于是大家就打听阴河的事,按七星布局,岩岭上该是七星之头,是我们这条冲的水源之地,从那里开始修水库,不就是从源头开始么?政府科学!
岩岭上是我们乡与砂石乡的分水岭,离我们村大约5里路,我家大姨就在那里,大姨与母亲最是亲近,你来我往的,那一带很是熟悉。大姨家就在岭上,屋脊后就是耸立的石山,一镞镞朝天矗立,莲花瓣一样开着, 屋脚下则是深渊一般陡立的山坡,这山坡与水库大坝连在一起。
修好的水库命名乌龙岩水库,水一直储不满,总是刚盖个底,于是解释说,水库底还是有阴河,水都从阴河走了。好在山冲有山可靠,石灰煤炭勉能糊口,大种水稻的政府命令也就只是敷衍敷衍,储不了水的水库虽耗了无数的工死了不少的人,村民们并不太怨,本来就没抱什么希望嘛。但有时也骂两句娘,因为岩岭上的人忽然发现自己晕山了,以前就算站在最高的山顶往下冲,也没听说过谁晕山,但大坝修好了,站在坝顶往下看,五六百级台阶,就像挂在空中,软软的飘着,风从脚底起来,将人直往上吹,脑袋再不是搁在颈子上,而像拨浪鼓一般被风摇晃起来,血往太阳穴直涌,晕,晕,村里人开始感觉天旋地转,站立不住,才知道,乌龙岩水库修坏了,破坏风水了。
我也是这批晕山中的一个,每次从大姨家回来,都要做恶梦,都要从大坝倒栽下去,都要从梦中惊醒。与山里人一样,我也不能理解,为什么他们的屋子像悬空寺一样斜挂在山崖之上,人却安安稳稳过着日子,而那处大坝稳稳当当立在两山之间,人站在上面都总是摇摇欲坠。或许因为开山修库,山体树木草叶全剃光了,秃头秃脑的,一山的灰石怪模怪样,青石跳宕,黑石摇晃,白石排荡,乌石瘫痪,千种动乱万般狰狞,将人的心扯乱了,才叫人心头发慌,脚下发软吧?
但脚下发软的山里人不会这么想,他们认的理是乌龙的理。认为乌龙被人扰了,才作祟人间,所以,得找到乌龙洞,得祭祀。 岩岭上是有人进去过乌龙洞的,那是个溶洞,但修水库时给破坏了, 那些去过溶洞的人也就只能记起自己的传奇,却再也找不到乌龙栖身的溶洞了。
那还是走日本时期的事,日本人来了,没地方躲,也就只好往洞里的藏,全村老老少少,牵牛带狗地,直往岩洞的深处去,也不知走了多少天,走了多少路,反正是只要有路,只要还能再进去,就往前进,只走到听到阴鸡叫了才打住。
阴鸡是什么?没人见过,但叫声与家鸡一样。听到阴鸡叫声,村民们就知道不能再进去了,否则触犯了阴界,触犯了龙神,大约是不得原谅的,毕竟那是另一个世界,人类不好太打搅。于是,在洞中躲一段时间,看看外面平静了,就土蜂出洞一般,一村人就都出来,重回人间。
出来的人辨认下方向,说听到阴鸡叫的地方在正西,大约有四五里地的样子,那该正好是我们家乡的方向了。于是,大家猜,地下阴河是往我家方向的,至少有五六里长。这与地面所见水脉一致,乌龙大约沿着阴河到西边来了,大家也就将心安下,开始在这边寻找乌龙。
人类与土地的联系,并非仅是物的,更是精神的,当大地的原貌被战天斗地的时代彻底改造,人的世界也就破碎了。好在精神的东西属灵,属于星空下的传说,人类靠着这暗淡的夜光,保持着大地的关联,保持着阴与阳的平衡。
不过那已经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,还得道士或巫师这些专业人士,那故事,我在《有井水处》已经讲过了。
我们这边,除了七眼井,还有与乌龙岩一样的一处水潭, 地称石翁塘, 石翁塘的水是常满的,水中时常浮现出石人、石马、石兽来,风行水上,涟漪波动,那些石头的走兽人马也会随着行走,坐立,涌起,游动,电影中影像一般扮演出各种姿态,生如栩栩,活过来了。
古老相传,这些石头原来都是活的,每每夜半人静时,会成群结对出游,平时与乡民们相安无事,阴阳边界各守一半,互不侵犯,但不知人类哪里得罪了(风水破坏),一次夜半出游,这群阴界的石兽就把一条河冲里的稻苗都给啃了,乡人没法,请师公作法,师公自然是知道天机的,原来,这群精灵藏在地下阴河,河马一般,属于夜间动物,白日里是不出来的,要降服它们,得入阴河才行。
于是有了地方上的勇士冒险下阴河,大战地下精灵的传奇。
那故事,我在《有井水处》里已经讲过了,这里要说的,是我个人的阴河历险记,想来,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风物传说,但一般也就当故事听闻而已,但经历过这次历险的我,才终于意识到,传说也好,神话也好,之所以能流传下来,不是因为故事好听,而是那故事中隐藏着一个永恒的召唤,它必然选定某个孩子听从它的召唤,走向它的世界。
那年,我十四岁。
翻过杨家台,跨过罗堂屋的一条水冲,就是周边最高的山,叫仙人岭,海拔五百多米,行政区划属于周官桥乡先锋村,讲风水则属于我们的朝山,我们村与这山下的坳上屋总是互通婚婚姻,彭姓与邓姓联姻,已经有好几代了。 我家大姐就嫁在仙人岭南的坳上屋, 坳上屋后的山坡上有一处溶洞,叫仙人洞,传说洞中有蟒蛇,但蟒蛇没得道,自然不能成仙,因此仙人洞里也就没有仙人。传说还有地下阴河,阴河与我们那边的阴河相通,最后通到宝庆府那深不见底的老龙潭,那里面是龙宫。
那时我在县城一中读高一,不知道为什么(大约是团支部组织春游吧)就带了一次大队伍,足足20人,以拉练的方式走了七八公里,从学校走到仙人岭,登上山顶,再从山顶下到姐姐家休息,告诉姐姐帮我们准备中——我们要进仙人洞。
入口是个竖洞,洞中幽深黑暗,不知深浅,但从洞底升起一块凸起的石头,似乎从黑暗中冒出来的一个柱子,要进洞,就要跳到这根柱子的头上,如果跳得准,刚好落到石头顶上,则可以平稳下降至洞中,要是第一跳就没站稳,那就有滚落深深渊危险——其实地下阴河就在石柱根部。
顺着石柱爬下去,就发现石柱是从地下河长出来的,河里有水,能听到潺潺流水声,凭听觉,能辨识水流的方向,我们虽带着手电,但光线不强,无法探知深度,只好避开阴河,不敢向下走,这也是当地人警告过的,而是往山顶方向, 当地人说,在山的另一边有个出口,只要找到出口,也就不至迷路。
溶洞仅够容身,洞内阴暗潮湿,有蝙蝠见光便噗噗乱飞,好在不咬人。我们担心的是蛇,尽管说蟒蛇早就没有,但谁能担保没有别的小蛇呢?于是互相提醒,留意下脚处。好在溶洞虽窄,洞底比较平稳,经过之处尽是碎石,显然,洞内时常有落石,大约那洞还在发育吧?再往深处,就见有大板,平铺着,很是干燥,想来是当地人传说的仙人床了,过大板后,洞口越来越窄,窄倒需要侧身才能挤进去,挤进去后,是一处大厅,高不见顶,从深处伸出两块巨石,斜着叠在一起,中间留有一道石缝,用手电照看,要进入大厅,只有这条缝隙,别无它路,于是,我身先士卒,仰身侧转,把自己扭成一片翻转的树叶样子,往缝隙里钻。
十四岁的我还没有体积,面积也小,做出拟态树叶的动作来也没太大的困难,但缝隙似乎也没有体积,只是一个平面,在这个扭曲的平面,人是无法保持自己人的“走”姿的,只能横着身体移动,平移,靠身体的摩擦寸一寸“长”进缝隙——那时才真正明白“长”是什么意思——但最终还是被卡住了,前面的缝隙不仅变得越来越薄,且也像树叶一样卷曲着,那曲度,显然超过我们人体能达到的极限,显然不能再亲进去,但后面挪过来的同学却还在跟进,于是,这条缝隙就被我们这些树叶给塞满了,在上下两片巨石的夹缝中,进不得退不得。
“坏了”,我心里一沉,至今我都清晰记得那瞬间的意识,一种面对死亡时的空白,竟然没有恐惧,而是平静。没有慌张,也没有挣扎,不过也无法挣扎,手脚被上下石板固定住了,仿佛被捆在石板上,呼吸慢慢变得艰难——不知道是空气变得稀薄还是石头挤压了胸口,后面同学顿时惊恐起来,起了骚乱,但我知道,我必得保持镇定,不能稍有心乱,否则,大家都得葬身这处洞穴了。
“都-停-下。”
平生我第一次发布命令,绝对的口气,一字一字吐出来。
“等我一会”。
大约是那决绝的口吻,令全体静默了,只听见激促的呼吸在洞中回响。
我静下来,放慢呼吸,身体放松,变软,然后开始分解身体(不知道当时如何想到的),先是手臂,再是头,再是上半身,分节挪移着,一寸一寸地将分解了的肢体向缝隙里送,终于挪出一个小小的空间来。
我知道,只要头部能穿过缝隙,身体就可以跟进。而头部空间不大,总能在缝隙中找到放置的位置。
还真的成功了。我将身体搬出夹缝,到了洞穴顶部,进入斜石的上层,躺下,大口呼吸。别的同学则听我的指挥,后队变前队,原路返回,我则从石板上一路滑下,回到洞口。
洞中经历似乎很短很短,但出洞时才知道已经过了二小时,留在洞口的外甥吓得脸都白了,正准备去叫人,我们却像逶迤出了洞口——头发披散,一身污泥,一群溃兵样子
我们也是这样子回的学校,引来同学们围观哄笑。
但我们这群残兵败将却个个昂首挺胸,一身豪迈,仿佛那是一次凯旋!
是的,那是我们的凯旋,是我们的成年礼,它将我们的少年懵懂与大地母体连为一体,也将生与死的体验焊接在生命的深处。